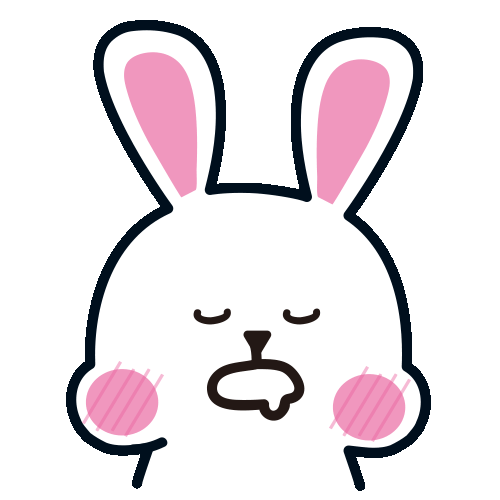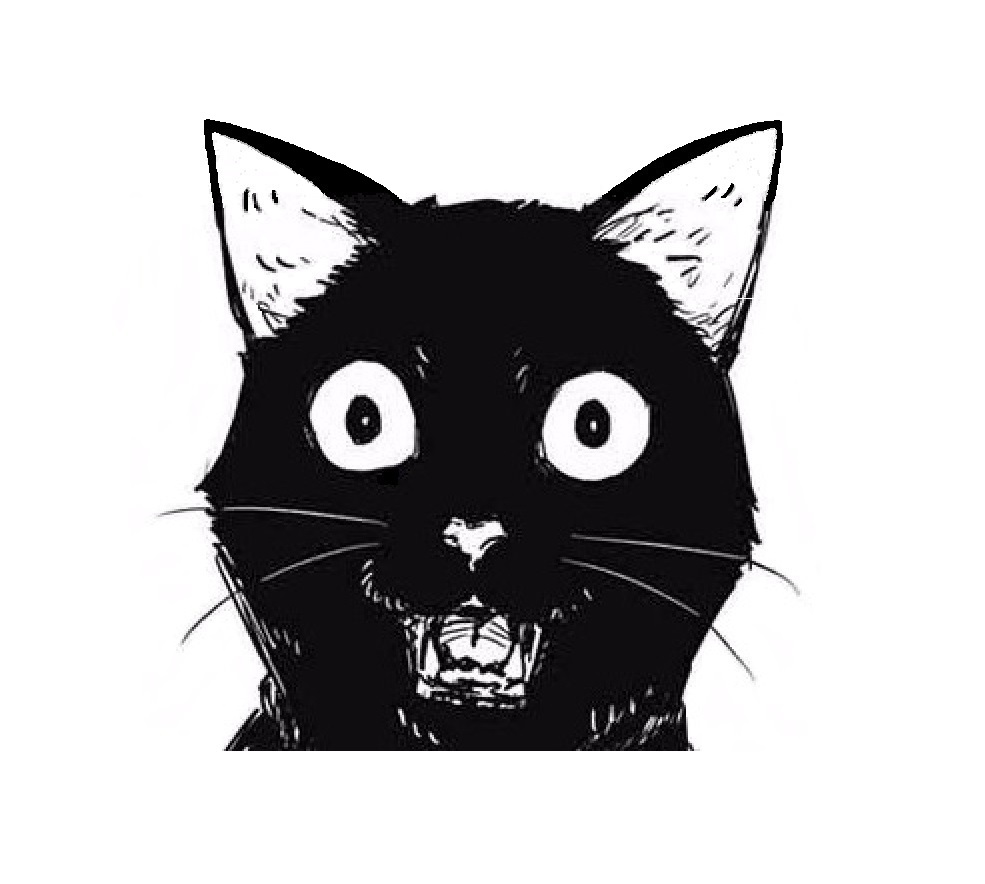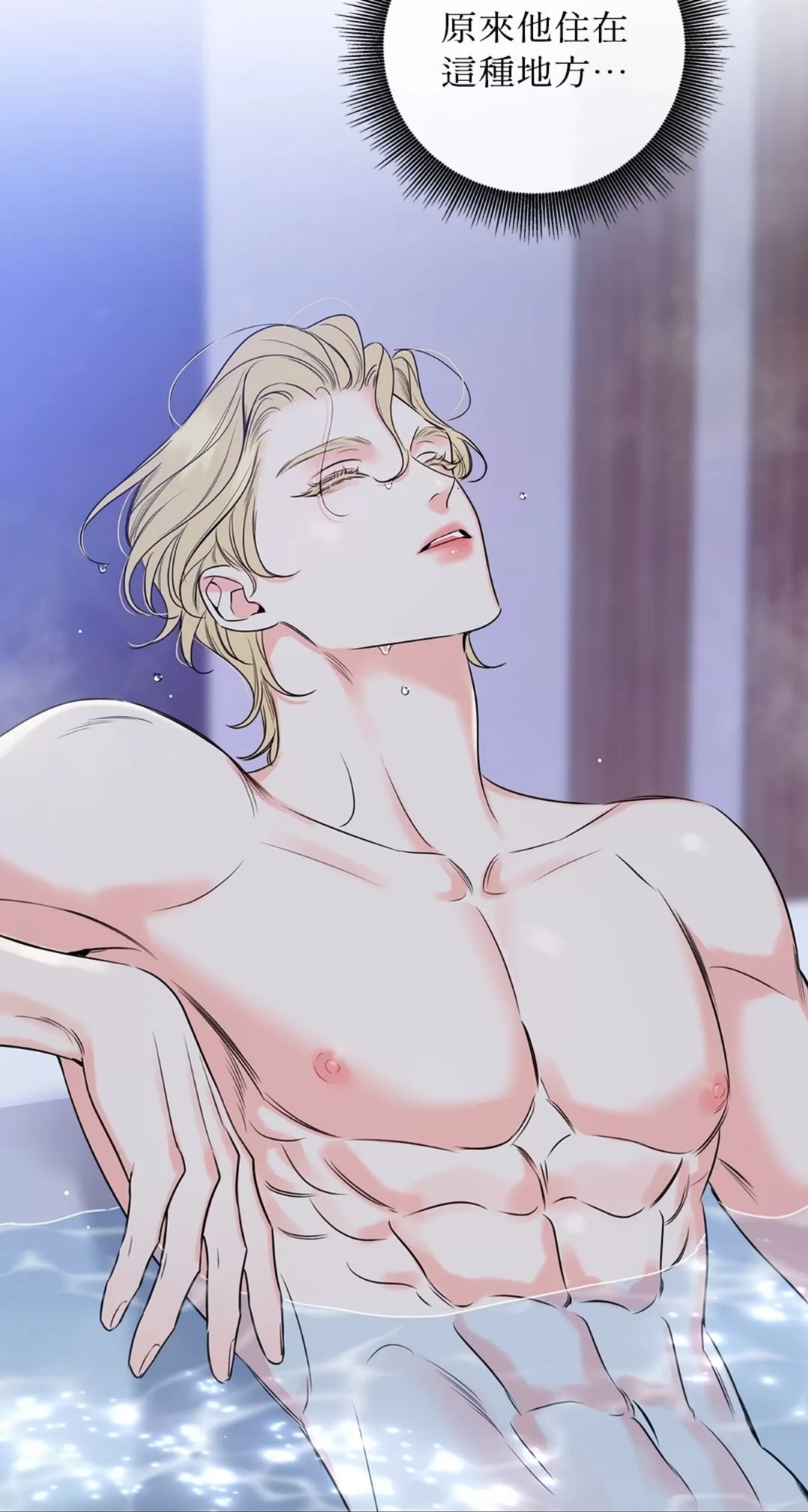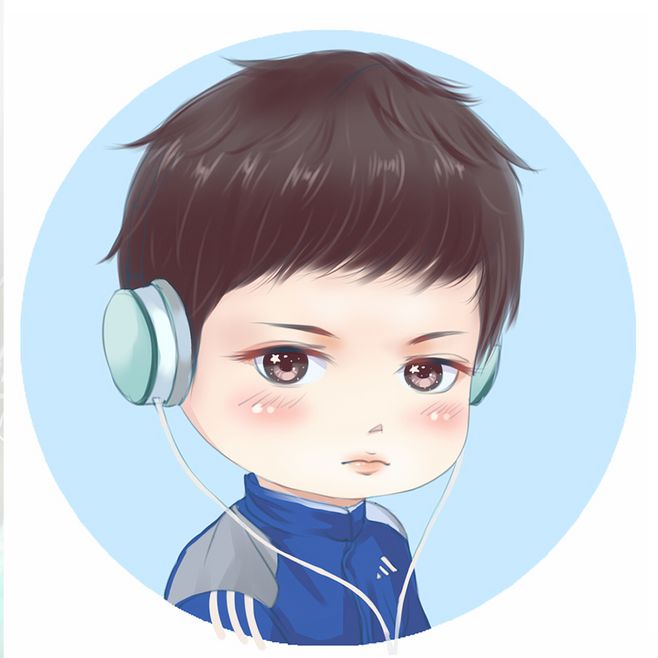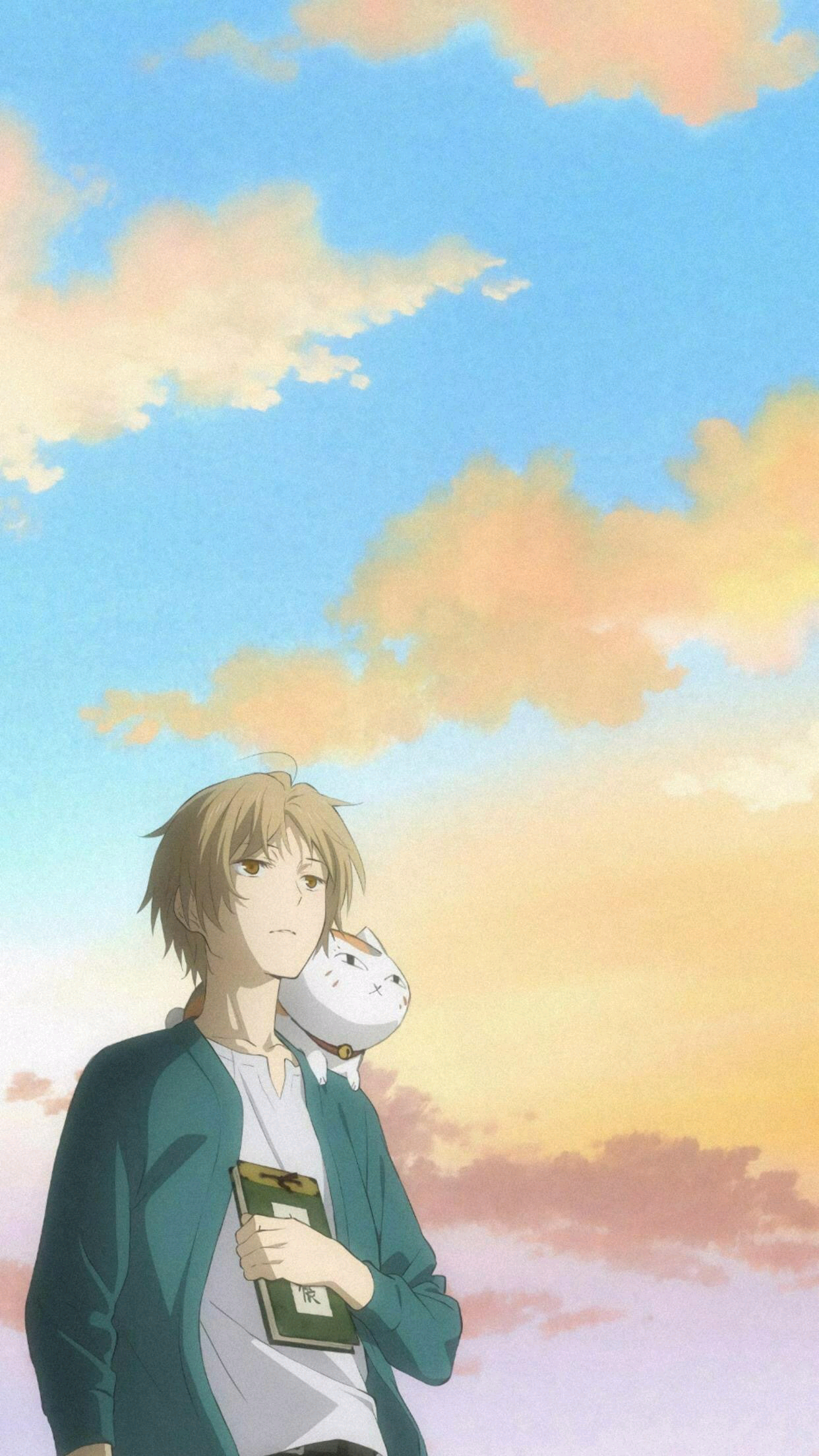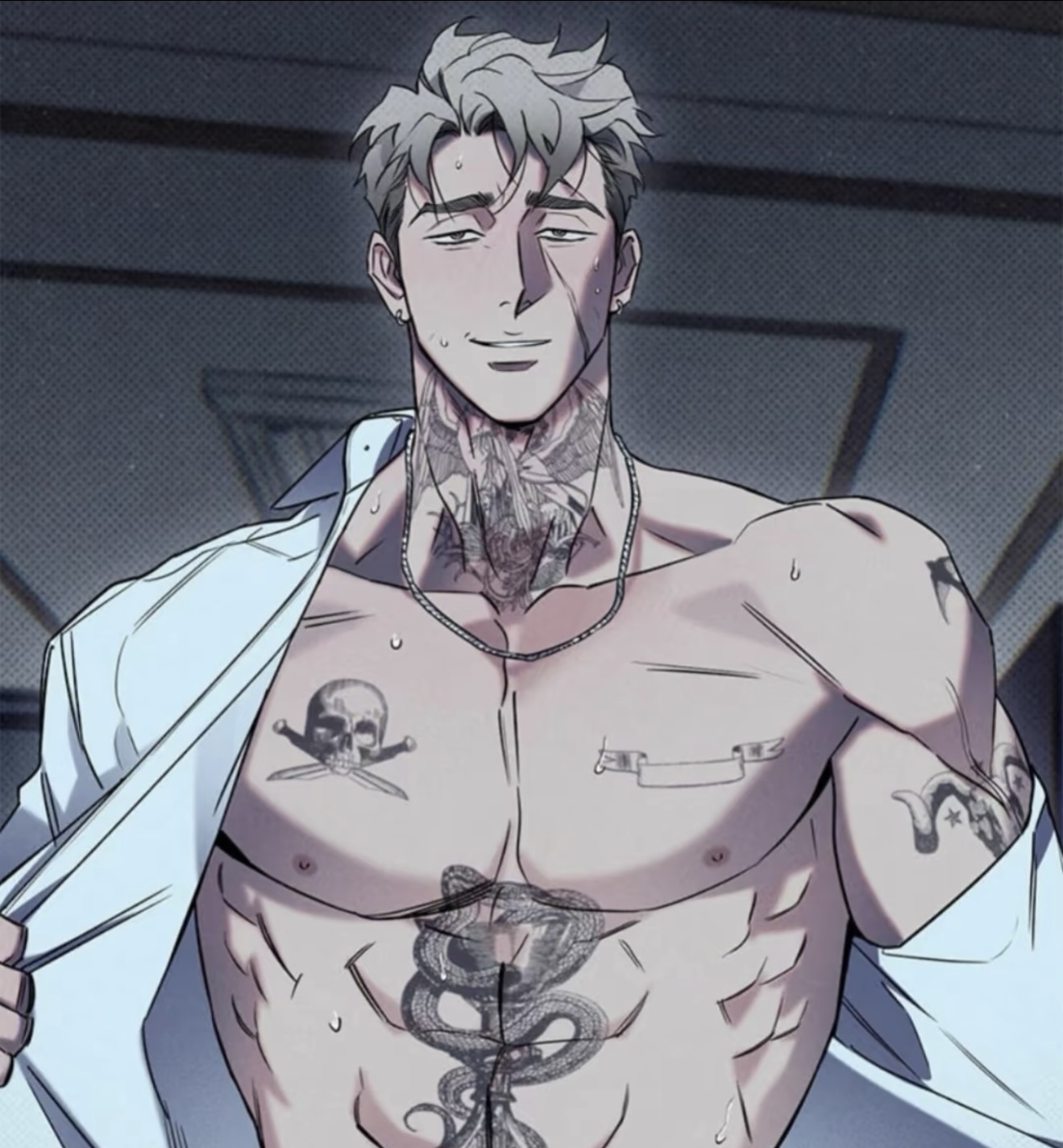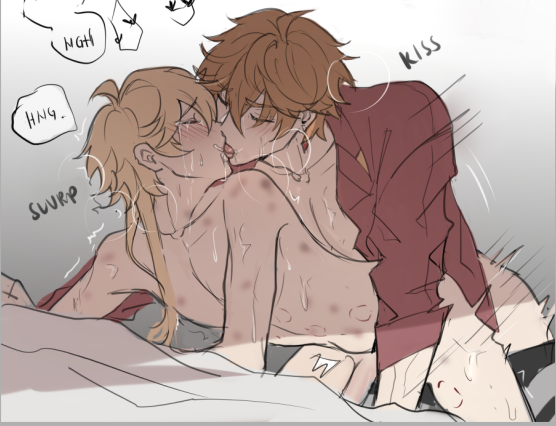2.白白的手。
砰,一声巨响。接着,血流成河。
“啊!”
捂着鼻子的阿尔塔紧紧闭上了眼睛,看着顺着手掌流淌的血液,瞪大了眼睛,发起了神经。
“这小子又使出了可耻的伎俩!”
“被欺负的人竟然是傻瓜……”
阿尔塔希望的是郑泰义正面回击他的进攻,与他较劲,但郑泰义明知会输,并没有多少想这样做的想法。这不是堂堂正正地进行比赛并以其实力来打分的测试,在实际的“打”和“打”的训练中,又有什么理由轻易挨打呢?
因此,他的攻击被他偷偷摸摸地挡住了,然后就在他脸上打了一枪,结果就乱成一团了。
阿尔塔说着什么,似听非听,他翻口袋递手帕,突然从身后飞来一只锅盖似的手,狠狠地抽打了郑泰义的后脑勺。
“阿药!”
握着被打得很响的后脑勺,流着眼泪回头看,和我的对手打了一局的卡罗,半是觉得很有趣,半是假装生气地站在那里。
“这样耍小聪明,总有一天会遭殃的。做对了,做对了。“
“……啊……。我已经听过五次了,这是我第六个通过小聪明的人了。“
郑泰义委屈地嘟囔了一句。然后阿尔塔紧挨着旁边嘎嘎叫了一声。
“要是早知道,怕谁遭殃!”
“事先知道的情况下,用正攻法也没人被打。”
郑泰义进行了非常妥当的辩论,但阿尔塔可能还是恼羞成怒,大喊一声。
郑泰义喃喃地说,知道了,知道了,离他几步远。然后突然撞到了站在背后的某人,停下了脚步。
“哦,对不起。”
“好好看看。你们队里那个吵闹的家伙也该怎么办。“
背上相撞的对方面带表情地说。是另一队的家伙。
就在郑泰义扬起眉毛,哑巴地盯着看的时候,那名男子拍拍被撞的肩膀,走开了。
“那是什么?”
“戈尔丁教官队的家伙。倒霉的家伙。“
“你认识吗?”
“脸和名字我都知道,但如果是问个人关系,我就‘不知道’。”
卡罗耸耸肩,摇摇头。可能是血还算止住了,还回手帕的时候,阿尔塔也发牢骚说“态度硬了一下”。
“你和那边的团队有什么不好的事吗?大家的态度怎么都有点生疏呢?“
“没什么不好的。虽然也没什么好处。本来就是这样。“
“原来?”
“比起合作,竞争的事情更多,能有好的事情吗?”
“……真是荒凉啊,小区……”
郑泰义摇了摇头。他和他的关系也不好,内部的团队之间也不好,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搞砸的。
在这里待久了会把人品都扔掉的。
郑泰义啧啧称奇,拄着颈道蹲下。然后第二次被打了后脑勺。
“哎呀!!”
这次虽然比卡罗打的弱,但被打的地方又被打了,疼痛倍增。正泰再次抱着头,这时郑泰义旁边再次响起了啪的一声,阿尔塔也跟着抱着头。
“对联中哪有坐着休息的。阿尔塔,你是大连的对手,对吧?如果你坐下来休息,我会在这段时间狠狠地揍他一顿。“
笑眯眯地那样说的人是弃性很久的叔父。
郑泰义泪流满面,用一双晃晃悠悠的眼睛盯着他,喃喃自语。
“三……,郑教官怎么在这里。现在不是教官的时候。“
但答案却没有回来。
正如郑泰义所说,现在应该在西侧3号讲义馆讨论战略论的叔父,不知是因为有其他事情才来的,走到了负责第二武道教育的教官面前。之后,一个男人瞥了一眼郑泰义,默默地笑了笑,跟在了叔父后面。
“哦,是司机。”
郑泰义脱口而出。
他和叔父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,从到达香港到到达这个岛的时候一直开着车。虽然现在穿的是室内制服,给人的印象比当年更硬一些,但肯定是。
“司机?啊,你是说康校尉?他会开你的车。“
“校尉又是什么啊。”
“跟我们是一个部员,说得简单点就是教官综合秘书。开车,帮忙干活,当护卫。“
原本以为很简单的阶级体系,越挖越多,就会有什么东西冒出来。
什么聚宝盆啊,郑泰义喃喃自语的耳朵里,是其他同事喃喃自语的声音。
“最近教官之间也产生了火花。我听说她和戈尔丁吵架了。“
“嗯,也是因为这个吗?总管营。我听说你要搬到总部去。“
“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为业绩而争吵了。不管谁当总管谁当次官,我们都无所谓。“
“也不值得那么心安理得地笑……。以前南美分部被推翻过一次。在水底激烈的明争暗斗中,应该也死了几个人吧。我不知道这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“
“嘿,够了,我害怕。你得照顾好自己的性命。“
“……”
郑泰义把下巴托在脖子上,静静地盯着叔父。在那样的对话中,我渐渐开始对叔父感到怨恨。即使这里的部员中只有一人死了,从打架实力和腕力等来看,郑泰义也属于最落后的。这等于是得到了第0顺位。
“果然靠的只有运气……。“再义,再义,给我分分那份运气吧……”
进入这里后,叹气似乎已成为习惯。
郑泰义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“哎呀”地站了起来。
阿尔塔进入下一个环节,新的大连对手回来了。因为是混队对联,所以对手不是自己队。还和陌生的面孔比了几次。
这次新回来的大连对手是刚刚被撞背的,戈尔丁教官的团队那个家伙。那个对手可能也认出了郑泰义,皱起了眉头。郑泰义啊……语无伦次地嘟囔着,挠了挠头。
我不想以这种方式熟悉他,但叹了口气,又抓住了他的脖子。即使是木刀,如果被比一般用的更重的木棍击中,即使身披防御套,也会痛得让人一刻也无法释怀。倒霉地被错了就是履行义务。
到达这里还不到一周,郑泰义已经去医务室逛了十多次。其中有四次是大连对手翻滚搀扶着去的,其余的都得他翻滚去。在地下2层,有讲课馆、实习训练场等,还有医务室,现在闭着眼睛也要去。
现在还算习惯了分部运转的系统。和队友们都很陌生,其他队里的家伙们虽然连名字都不知道,但也很熟悉脸。虽然也有100多名,但在正规课程时间里,有时还会互相殴打对方,因此,即使是被痛打,为了补偿,也不可能不熟识。
现在做的武道教育,每节课都有主题,今天是牧道。除了有效使用牧道的规定之外,这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无限接近于战斗的对联。
郑泰义窥探了一下男人向自己走来的缝隙。木道迎面一撞,一声硬梆梆的响声响了起来。同时,手腕也会有酸痛的负担。这个男人好像也很有力气。
“好吧,那么……”
郑泰义一把抓住对方的内领。然后照样转过身去。
踌躇不前的对手发现了郑泰义的空当,用木刀毫不留情地打了过去。疼得要死。大手大脚的,还不看情况乱使劲。
郑泰义嘴里捡起骂人,一边吞咽,一边忍住了那群毒打,把另一只手里握着的木刀扔了出去。然后双手一下子握住对方的衣领,从肩上扛了过去。
因为光着身子挨打是值得的,所以暂时反抗,摇摇晃晃的对方,最后背撞在地上,躺下了。
当男子躺在地上时,郑泰义又拿起了扔下的木刀,整理了衣领。刚要从地板上起身的对手眼中露出了惊愕的神色。
“嘿,你不会现在--。”
“好了,现在你也该挨打了。”
郑泰义说着很寻常的话,连袖子都卷起来,不经意地开始殴打男子。男子在挨打中也迅速起身,但其间被打的次数是他的两倍。
男子完全站了起来,停止吊打的郑泰义,只能听到男子在手臂或大腿边揉捏着,脸上红红的布满血丝的大喊大叫。
“嘿,你这个无知可耻的混蛋!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打架!!“
“说什么呢。你刚刚经历过。“
郑泰义一脸太平,眨巴着眼睛说。而另一边的阿尔塔--已经忘了自己刚才被人以类似的方式打了--却笑得耸耸肩。
满脸通红的男子没有脖子,只身扑向郑泰义。看到男子紧握衣领、紧握拳头欲抽打他的下巴,郑泰义暗暗皱了皱眉头,用手中的颈刀轻轻地将男子的脖子砍掉。
“哇……”
“明明知道对方拿着凶器,却徒手扑了上去,想怎么办……”你得考虑一下你的身体。“
郑泰义心疼地皱着眉头,循循善诱地说。男子一手抓着自己的脖子,也不放开郑泰义的衣领,摇摇晃晃地退了两步,结果郑泰义撕破了上衣。
“嘿,看他在说什么。让你想想身体想想身体。猫想老鼠。“
“恶毒的家伙。如果下次内行发生凶恶的事情,那凶手一定是那个家伙。“
身后传来同事们窃窃私语的声音。
郑泰义茫然地看着突然露胸的装扮,听到那声音就凶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
“我都听见了。”
“除非你的耳洞里有什么东西,否则你当然会听到。哦哦哦哦哦哦都能看见。“哎呀,粉红色的乳头真可爱。”
“……”
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和像大叔一样的人交往,只喜欢可爱的美青年。要是听到和我同性的家伙那样的话该多难受啊。如果是像蜂蜜一样的美青年,即使是乳头之类的一百个,也可以欣然作为诱饵,把他的身体全部钓走,但听那样的大叔说这种话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。
郑泰义愁眉苦脸,草草收拢衣服,把衣角捆起来。被郑泰义的脖子刀砍到脖子的那个家伙可能很疼,还像石像一样停了下来,攥着脖子呼哧呼哧地跳着。
“你为什么穿成那样?预算主任很生气。“
可能是干完活了,正在路上的叔父仔细打量了一下郑泰义,噗的一声笑了起来。
“衣服磨破了、撕破了,这对训练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啊。”
“那件衣服没有被磨破啊。不管怎么说,虽然看起来是绝景,但是视线都很尴尬啊。去找新衣服吧。顺便炫耀一下身材。“
叔父微妙地笑了笑,然后出去了。
从那以后,讨厌的声音就像“趁这个机会也能看到辛鲁的脸”、“顺便在他面前换上衣服来吧”、“晚一点来也会理解的”等,个个笑个不停。
对于其他事情,郑泰义能够保持近乎完美的扑克节奏,唯独在辛鲁面前,不知如何隐藏内心。看他那瞬间脸红、犹豫不决的态度,谁也别让他察觉,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正因如此,团队中没有人不知道郑泰义心系辛璐的事实。大概辛鲁本人也想知道。
对于这件事,郑泰义除了庆幸之外,还有一种感激之情。
同事们一开始看到郑泰义面对辛鲁的态度,都摇头,过了一会儿又不假思索地问:“你的爱好是你吗?”这时,郑泰义想了一下否定。这是因为想起了以前在军队时的记忆。
对同性拥有超过好感的感情或拥有肉体关系成为了严重的障碍。这也是他与同事关系不融洽的原因。
但也没想瞒过这些,也没觉得能瞒得住,郑泰义点了点头。认真地看着他们,
但是同事们的反应却非常平淡。“什么啊,原来是这样啊……”这两句话就结束了。
“在这险恶的谷底上滚了好几年了,那程度也不足为奇。不要太明目张胆。……啊。我喜欢女人,所以不要喜欢我!“
也许是理解了郑泰义困惑的表情,卡罗似乎很无聊地自言自语,然后用一副严肃的表情给出了忠告。然后忽然,他带着浓浓的笑容,慢吞吞地说。
“他说,我喜欢辛鲁。嗯--。你知道这是禁止恋爱的,对吧?
从他的话开始,从那以后,同事们都是这样。简直是百年戏弄。
面对同事们不严肃的敷衍了事的态度,回忆起过去的郑泰义感到欣慰。
但当然,当我听到那些慢腾腾地取笑我的声音时,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“如果你羡慕的话,就把你的衣服撕掉,一起去吧。这样我才能把那无精打采的身体交给谁呢?“
郑泰义厚着脸皮看着同事们,理直气壮地说。这时,就在刚才还在单身逗乐郑泰仪的同事们,单纯地马上就勃然大怒。
“没帅,没帅!看我这魁梧的肌肉!“
“这酷毙了的皮肤!倒三角形身材!所有的女人都死了!“
“你看起来很无知,没有平衡。……但也不是像我一样以粉红色的可爱乳头为卖点。“
郑泰义用露骨地嘲笑的眼光左岳地看了他们一眼,然后嗤之以鼻地走了过去,好像是让他们听。
背后是同伴们呼喊着的声音,但也不是一两次听到,只是和苍蝇的嗡嗡声不相上下。
***
回想起来,郑泰义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
虽然看着人心里怦怦直跳,但那个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感情就消失了,虽然有很多和别人上床的经历,但很难称之为恋爱。
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青年--就是那个动刀的主人公--主张说:“我们不是交往的对象,虽然想想以后的行为,这是无法理解的事情。”所以,其实在和那个青年开始相处的初期,郑泰义也有过自己的伤害。我想我和谁的命运只能是简单的关系。
从那以后,就没有遇到过能直击心脏的对手,而且军队生活变得艰难,也没有闲暇去想别的事情。
所以,这种感觉很陌生。但还不错。即使是暗恋,心情也很好。光是看到某人就能让心情变好的经验。
“对不起--”
走进办公室,郑泰义说的时候,里面有4名男子。三个交互,一个次官。
郑泰义在进入这里的第二天,看到结束了形式上的问候的那位次官,端正了姿势,轻轻地行了个注目礼。他可能是刚办完事,向郑泰义点点头接受了问候,然后从他身边掠过。
鲁道夫·让·蒂尔。是个男人,他是我叔父的顶头上司。
因为和郑泰义只是在形式上短暂地打过招呼,所以对他不是很了解,但是听周围的评价,他是一个看似软弱,却不能小看的人物。
郑泰义怀疑地反问:“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他是个黑心的家伙?”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。
怎么也无所谓。只要是半年来只关心自己性命的上司,就算心里黑乎乎的烂掉了,也不会介意。
“泰哥?你来这里有什么事。……你的衣服怎么了?“
郑泰义暂时望着次官的背影,听到温柔而熟悉的声音,他转过头来。
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的辛鲁看到郑泰义的打扮,脸上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。
“嗯?啊。对联的时候。我来拿新衣服,你没事吧?“
郑泰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摆弄着撕破的衣角。辛鲁回答说:“当然了,”然后站起来走进办公室里面的外间,拿出了新衣服。
“谢谢。这件衣服怎么办?你是把它脱下来拿给我,还是把它扔掉?“
“嗯……。这样破了,修补起来也不方便。我想你可以直接扔了。……你没有伤到什么地方吧?“
“受伤是家常便饭。没事的,没事的。谢谢你的关心。“
郑泰义不好意思地笑,辛鲁也微微一笑,低声说:“你要保重。”
在这个分部里,年纪最小的辛鲁,那天在浴室碰面后不到一个小时,看到再次站在眼前的郑泰义,吓了一跳地僵硬着脸。但那也是暂时的,不知是多少次碰面聊天之间,解除了界限,叫郑泰义为哥哥,亲切地跟着他。
“……”
就在眼前看到了申楼的头顶,她一边抚摸着被撕破的衣领,一边掂量着是否修补。从鼻尖掠过的味道是隐约的肥皂味。我想摸摸看。
手指头一缩,苦恼要不要碰一下头轿的郑泰义,因为申楼抬起头来,赶紧把手放下,打消了念头。如果叔父看到了,他会骂我是个没胆量的家伙。
“今天也辛苦了。离正常工作不远了。“
辛鲁那样说着微笑着,这才让郑泰义意识到时间已经晚了一个下午。转过头来,窗外,天空中泛起了微红的云彩。老呆在地下,不看表就找不到时间感。
“天色真漂亮……”
郑泰义感叹道。并不是因为只呆在地下看不到天空。实际上,青蓝和红紫色相得益彰,在天空中混合的颜色非常漂亮。
“这里,外面有蛇?”
“什么?是的。晚上很上镜。但森林那边就是这样,到岸边就好了。“
“嗯--。你想和我一起去吗?“
“……现在吗?”
辛鲁似乎有些慌张,小声地反问。郑泰义笑着点头。而且内心也很佩服自己。
我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随便约你出去。我是说,我不是那种满脸通红,像个傻瓜一样呆着的人。别看这样,我在俱乐部里以手快着称……不,这不是好事,算了吧。
虽然是自以为欣慰的郑泰毅,但他的脸已经熟得通红。
辛鲁盯着他,做了一副奇怪的面孔。又像是强忍着笑,怎么看又像是为难。看到那道光,郑泰义有些退缩,但仔细观察,似乎还是没有带不愉快的光,还好。
“嗯……,你不喜欢吗?”
“与其说不喜欢,不如说工作还没有结束。哥你自己去一趟吧。我觉得风吹得很好。“
辛鲁哈哈大笑,摇了摇头。郑泰义虽然很沮丧,但他还是努力看不到那种光芒,喃喃自语道:“是啊,原来如此。”突然间,天啊什么的,心里闷闷不乐。
本来想一个人出去看看,但当我无缘无故地膨胀起来的心一熄灭,我就不再想那样做了。一个人随便请,一个人随便期待,人真是个任性的生物,郑泰义内心苦苦地笑了。
“好吧,那我就好好工作,再见。加油。“
“是的,泰哥。……啊,嘿,兄弟!“
郑泰义转过身,走出办公室,走着走着,不知是否犹豫了一会儿,辛鲁走到办公室的门槛,把他叫了起来。然后一脸诧异,嗯?对回头看的郑泰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。
“明天或后天,我们一起去吧。我知道一个很少有人来的地方。“
“嗯?……呃……,真的吗?“
“是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“
“哦,是我,当然没关系。……是的,是的。任何时候。你完事后叫我。我结束正常工作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。“
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,郑泰义虽然慌张地笑了笑,但也赶紧点点头。然后就白摆弄着支部发放的寻呼机,非要补充一句:“什么时候联系都行。”
“是的,”辛鲁笑着打招呼后,再次走进办公室。独自留在走廊的郑泰义呆呆地望着他站的地方,然后无声地猛地握了握拳头。
你看,这话值得一说。不管怎么说,就算今天不行,明天和后天也只能见两个人了。
郑泰义虽然想忍住,但最终还是放弃抹去嘴角不断升起的笑容,转过身去。
我很快就感觉好多了。也会有心情走出去,带着愉快的心情环顾四周。
不过马上就会和辛鲁一起出去,为了那个时候,还是省点出门游玩吧。
郑泰义哼着歌,步履走向电梯。但在等待停在地下五层的电梯上来时,他摇了摇头。
还有一点正常工作和时间。按照原来应该回去,但是当初想跟辛璐翘课的身体。因为是现在,所以没有想过再回去拿一副对联。
不归,以后颇受惊扰,已浮的心却不愿再归。
“……那个时候还是在食物丰富、读物丰富的房间里翻滚……”
自言自语的郑泰义在电梯前转身下楼。
他的目的地是叔父的房间,那里有丰富的食物和丰富的读物。挂在指尖上的钥匙在口袋里开心地晃动着。
从地下一层下来到叔父的房间,一路上和往常一样,没有碰到任何人。真是人迹罕至的楼层。在这里,即使发生了谋杀,也不会有一阵子没注意到的--不可能吧。到处都有监视器。
郑泰义一边指着安装在不太显眼的地方的摄像头,一边走向叔父的房间。在走进叔父的房间之前,他礼貌地向其中一个照相机打了一下电话,然后敲了敲房门。
我没有敲门。反正里面要是有叔父的话,门不管怎么看都不会锁,要是没有的话,门就会锁。因此,至少在要求开门的意义上,这是不必要的行为。但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告知他已来的手段。从他转过拐角的时候,叔父就已经意识到有人正在向门外走来。
敲了两下门,稍微隔了一下,然后拉了一下门把手。门是锁着的。郑泰义悄悄地扬起眉毛,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。是日前在房主允许下拿到的钥匙。叔父爽快地把钥匙给了他,让他在任何好的时候都来读他想要的书。
房间里像往常一样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你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,但有时你甚至感觉不到你还活着。
“叔叔居然也有荒凉的角落……”
干净得一尘不染的房间,叔父不在的时候总有这种感觉像是无人居住的模特房。这种感觉与叔父的反面很相似,郑泰义叹了口气。
随便打开冰箱,从里面拿出一罐啤酒,一口气灌了进去,郑泰义一头扎进了整齐得没有一丝皱纹的床上。在弹力刚刚好就能接触到身体的床上翻滚了几下,那里才有了人情味儿。趴在上面,从触手可及的书柜里拿出一本书。
每天结束正常的工作,如果没有别的事情,就会来这里打滚看书。每天几十页,每一篇文章都在慢慢回味。
看到这个书柜里堆满了很难找到的书,我想郑在义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书柜。不,也许他已经读完这些了。
我没有理由担心那个幸运的人,但我很好奇。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呢?回到家了吗?呆在哪个图书馆或研究所里,几天几天不睡觉地埋头看书?
我昨天试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但没人接。虽然是接近午夜的时间,但他还没有接到电话。从这一点来看,他应该认为他还在某个地方闲逛。
突然想起了他一边用手指剪断缘分线一边用手指剪断的样子。
我真的不认为他讨厌自己,也不认为他想和他断绝关系。但该怎么说呢。那一刻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他本来就很幸运,是一个一切都能如愿以偿的哥哥。所以,如果他装出要断绝缘分的样子,他和自己之间的缘分真的会断绝。
也许在那一瞬间,他和郑在义的缘分就被切断了。那么以后就再也不能见面了吗?
“我不喜欢这样……。我感觉不到什么。“
郑泰义躺着,展开手看着。就像哥哥说的,也许是绑在小指头上,寻找看不见的红线的痕迹。但它真的能被剪掉吗?
郑泰义啪嗒啪嗒,小指头啪嗒几下。就像在观察看不见的红色丝发是否会轻轻飘动一样。
就是那个时候。安静的机械声传到了呆躺着只盯着手的郑泰义的耳朵上。这是以前听过的声音。转过头来,电话里的灯亮得通红。
“……”
呆呆地盯着不断闪烁、发出机械声的电话,想了一会儿能不能接别人的电话。其实我知道不用多想就不接听从各方面来说都很方便,也不会有后顾之忧,但电话响得真够死缠烂打的。
郑泰义下床看了看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来电显示号码。虽然郑泰义连能给叔父打来的号码都不知道,但还是慢慢揣摩着那个陌生的号码。
这是国际电话。如果是以49开头的号码……是德国吗?后面的数字可能是区号,但我不知道。
与此同时,电话中断了。郑泰义又回到床上拿起书。但是对哥哥的思念一浮现,就一直没有消失,就用书盖住了脸。哥哥经常这样睡觉。我问他重不重,但他反问:“几百页的书有什么重?”每次都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脸上睡觉,但看到五官完好无损的样子,真让人感到神奇。
这样看来,他和哥哥不太像。虽说是双胞胎,但没有与之相像的地方。脸也好,头发也好,性格也好,运势也好。
“……。但是脸还是我更好。即使其他事情都无法应付。“
事实上,长相本来就不同,谁长得帅谁长得丑都没有机会。
郑泰义从脸上把书拉下来一点,转移视线。虽然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看不到他的身影,但书桌旁挂着一面大镜子。
郑泰义又站起来,朝那走去,把脸紧紧地贴在镜子上。一个面容平淡的男人映照在镜子里。还没过半辈子,也许有点累了。
把自己的脸扫过镜子。冰冷的镜面手感传到指尖。
眼睛,鼻子,嘴边,就这样摸索着,灯又闪了。几乎同时,机器声也会响起。又是同一个号码打来的电话。
这次没等太久,就接到了电话。这样接二连三的电话,不接不一会儿又打进来
“是的,喂。”
按下灯,显示器亮了。然后里面可以看到听筒那边的画面。
什么都没照到。是白墙。在屏幕尾部,乍一看就能看到相框的一角。这幅画的颜色用小屏幕看不清楚,不知道画的是什么。
“--哈哈啊。又是你侄子。“
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。接着在画面中,可以看到伸到电话前扶着桌子的手。那只手我记得很清楚。这是一只美丽的手,让人难以忘记。
“哦,是手。”
“什么?”
郑泰义半丝半丝地脱口而出,另一边似乎很诧异地回了一句简短的反问。
“手。”
郑泰义一声觉得答错了,却一脸无所谓,轻轻地拍了拍显示器上那只白色的手。手在监视器里移动。好像在看自己的手。
“你的手真漂亮,很快就会记住。”
“哈哈,谢谢你。你的手被称赞了,你会高兴的。“
在监视器的另一边,男人笑了。虽然仍然是机器声音,但并不像第一次听到时那样刺耳。
“郑教官又在洗澡?你可能经常去那里,侄子。
“不,叔叔不在。我只是来读书的。我叔叔的房间里有很多书可以读。“
啊。“郑教官的爱好不错。”
白色的手似乎很开心地轻轻地拍着桌子。玻璃般光亮的指甲显得异常冰冷。好想扫一下。每根手指上都挂着冰凉的玻璃碎片。
‘那么喜欢我的手吗?’
“嗯?”
‘用好像要吃掉的眼睛看着呢’。
他含笑地说。郑泰仪也噗通一笑,缩了缩肩膀。
“有那么露骨吗?不,我想是的。这对我来说并不合适。“
他还想说死后要给他割腕,所以提前补充道。他可能猜到了郑泰义的想法,愉快地笑了。
郑泰义忽然斜了头。据说看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那个人的生活,这个男人怎么也搞不懂。我不认为我会做粗鲁的工作,但我也不认为我整天都在工作,手握笔。古籍经销商也会有自己的脏活干,但他的手头根本没有脏活
“伊莱……?”
郑泰义开口了。这样看来,这是我第一次叫这个男人的名字。男人还是带着笑意的声音自然地回答“嗯?”
“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了叔叔,他有点迷茫。看起来有很多名字。“
“啊哈,是吗?当然,郑教官不会叫我第一名字。名字是哈娜。我没有做坏事,我没有理由写很多名字。“
“嗯--如果是古籍中介的话,可能是……做什么事情。”
郑泰义打断了一下。拥有那样的手的人会做什么事呢?
随后,男子暂时一言不发。只见白色的手轻轻地、轻轻地敲打着桌子。与其说是不高兴的神色,不如说是在静静地望着这边,沉思着。镜头外凉爽的视线。
过了一会儿,他似乎想了个小主意,缓慢地回答。
“有时我会帮哥哥处理家业。也许那件事由哥哥来接,我不知道……,做什么来维持生计呢。我从没想过,但听到这个我很担心。“
听到那个完全看不到担心的光芒的声音,郑泰义突然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。
如果半年后从这里安然离开,无论如何,自己都是没有工作的无业游民。当然,按照叔父的说法,只要是在这里工作的经历,就业就不会有任何困难,但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呢?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
“转业后完全成了废人……”
他深深地叹了口气,喃喃自语,好像那个声音连那边都听到了。
“退伍?”他是个士兵吗?当然,有时也有人在军队里,然后去那里。但是很有趣。因为郑在义的弟弟是军人……。哈哈。“
那人喃喃自语地笑了。郑泰义悄悄地扬起眉毛,看着他雪白的手,扑哧一笑。
“为什么。“脑力派的哥哥下面竟然是肉体派的弟弟,可笑吗?”
男人这次才放声大笑。笑得好像看了一场很棒的喜剧似的,然后慢慢地挥动那只白皙的手。
“不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而且,我想你的身体不够魁梧,不能自信地说你是个体魄派。如果是其他意义上的“肉体派”又不知道呢?“……这是个失礼。”
听到男人的笑声,郑泰义一脸苦涩地说:“没关系,”。
“不,我的意思是,在开发武器的哥哥下面,被武器牺牲的弟弟这个组合很有趣。”“如果是军人,与其说是使用者,不如说更接近牺牲者。”
郑泰义托着下巴停顿了一下。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男人说得很寻常的内容。
后面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前面几句话。
男人也看得出郑泰义盯着雪白的手的表情变得很微妙。然后想了一会儿,他可能也明白了其中的原因,尴尬地嘟囔了一句。
“哦,天哪。你不知道吗?
“……是的,我不知道。我哥哥参与了武器开发?“
郑泰义笑着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的东西,别人更清楚啊。”但是,郑泰义觉得说不出话来。
郑在义和郑泰义虽然不是关系不好的兄弟,但也不会一起分担所有的事情,可以说是关系适当的普通兄弟。而且郑泰义从高中毕业开始就很少呆在家里了,郑在义也经常不在家,彼此不太了解对方的生活。到了这里才听说他是UNHRDO美洲本部也特别对待的研究员。
但是武器开发。
什么时候做的。如果是在UNHRDO吗?但也许在这之前或之后。不管怎么说,关于工作的话题,彼此都不感兴趣,没怎么聊。
武器。武器。
郑泰义苦笑。虽然知道这是必要之恶,但是郑泰义看到了太多的负面影响。
“我想我说错了。“谁知道谁就知道,但这只是机密,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。”
“我也不想亲口说我哥哥在开发武器。”
“哈哈,看来你不喜欢。但你哥哥是业内公认的天才。“
“就算是做武器的天才,也不太高兴。”
就这样发牢骚的郑泰义忽然扬起了眉毛。然后摸了一会儿下巴,噗地笑了。
“一看是这边行业,你也从事军火相关行业吗?”
那人又沉默了。这次的沉默有些漫长。如果不是偶尔移动的手,你会以为电话断了。
不一会儿,他就像叹息一样笑了。
“确切地说,我哥哥在那里工作。你说过你有时会帮助你的家庭吗?“
“家业是军火行业?”
郑泰义一脸无奈地反问。然后我意识到。这个男人不是古书经销商之类的。经销商虽然是经销商,但所涉及的物品不是古书,而是武器。
“看来你是靠卖武器生活的……”
“不是我,是我哥哥。--你看起来很讨厌。这几年销量排行榜上不折不扣的就是你哥哥设计的基础火箭炮。“
“我的真。所谓没有战争的世界,到底是生活在哪个命好的国家的梦境居民的狂吠声……“再的哥哥,见了我就揍你一顿。”
男人笑了。那个在郑泰义脑海中掀起了短暂而严重的波澜的男人,看上去毫无距离,泰然自若。
“好可怕啊。”好吧,所以你要和你的哥哥断绝关系吗?“
“这算什么。缘分是你先断了。“
“啊哈?”
那人的声音变成了有趣的光。我想看一眼那个人的脸。一定是带着缓慢而微妙的笑容盯着屏幕。
‘没想到是关系那么不好的兄弟。我以为关系还不错呢。怎么,你打过架吗?“我没想到郑在义是我先向弟弟提出断绝缘分的人物。”
“女-基上的线啊,我说我要把它剪掉,然后那天就离家出走了。他仍然下落不明。“
郑泰义抬起小指头,喃喃自语。这不是事实,但这就是重点。然后男子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。
‘HAHA,是郑在义说的吗?’这很有趣。“
“这对你来说可能很有趣,但对我来说却是家庭破裂的危机。”
“哈哈,啊哈哈哈哈。”
男人不知什么事那么开心,连连笑了起来。机器声音的笑声太奇妙了。
“你一定很开心吧。”
“不……”我想这是另一个兄弟。因为是双胞胎,所以觉得应该有相似的地方,但是这个脸也不一样,性格也不一样。这很有趣。“
“--你和你哥哥见过面吗?”
“嗯,只是一张脸。我很惊讶,因为我比我想象的要年轻。“
那已经经历了好几次了。从小,无论什么途径,听到郑在义的说法,好不容易找上门来的人,都被他吓了一跳。很少有人表示:“没想到这么年轻。”
但我想这个人也不会太大。
郑泰义盯着那只白白的手看,虽然光用手是不可能知道年龄的。
但没有想过要追究那么个人的事情,就把话说回去了。
“那么说的那一方,跟那个做武器买卖的大哥长得很像吧。”
“嗯。虽然没怎么听说长得像,但我和哥哥不是双胞胎。年龄差也挺大的。“
郑泰义斥责说:“兄弟之间长得像不像,年龄差有什么关系。”他摆摆手。
然后那人停住了。微微转过身来,似乎有人在他身后或有什么声音。说是帮助家业,不知道是不是和家人和睦相处。
“这很突然,但我得走了。那我们以后再见吧。“
“哦?啊,嗯。呃,那你叔叔呢?“
“我待会儿再打给你。“拜拜。”
白白的手微微一摆。然后电话就断了。显示器又变暗了。
郑泰义叹了口气,再次按下灯。一瞬间,周围安静了下来。
啪啪,啪啪,就像刚才那只白皙的手在显示器里那样,郑泰毅也默默地拍着桌子,像石像一样站着。我觉得我的头脑会变得复杂。但如果换个角度考虑,现在郑泰义的头脑并不复杂。
“唉……。不知道。我只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。也不是反战运动。“
“是的,虽然我已经辞职了,但世界上职业军人也很多,他们也得养活啊……”郑泰义自言自语地一头扎进了床上。
猛的一下,把脚背踩在了床角上。疼得死去活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