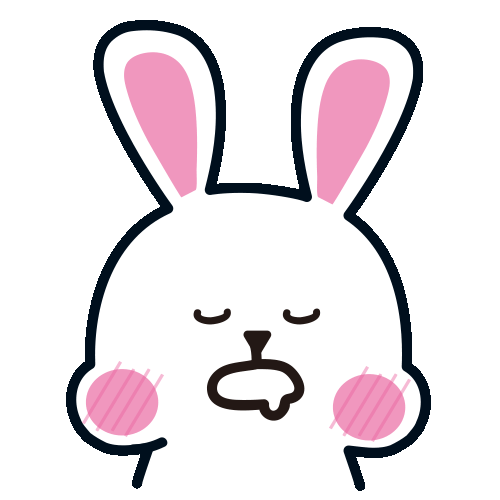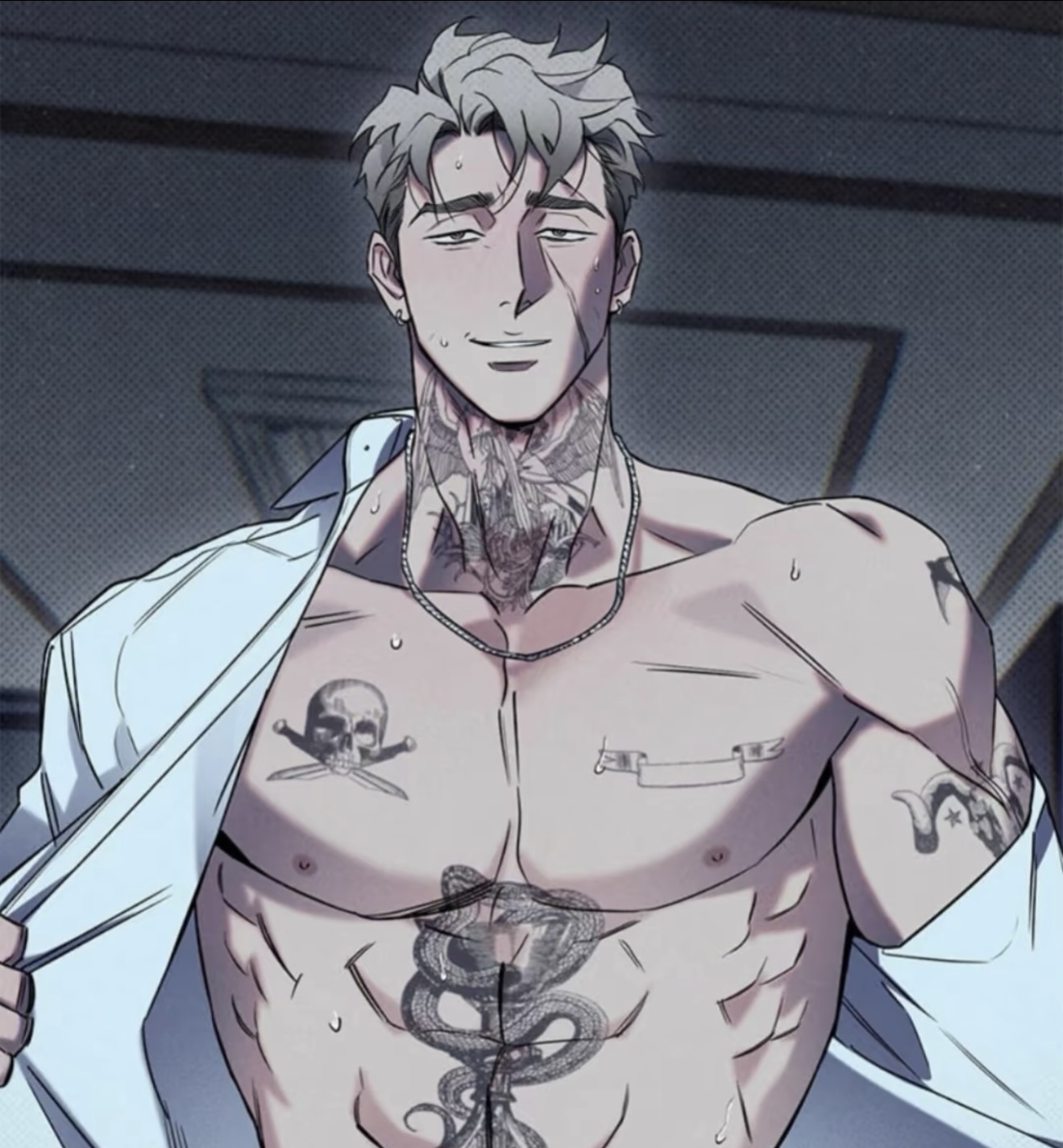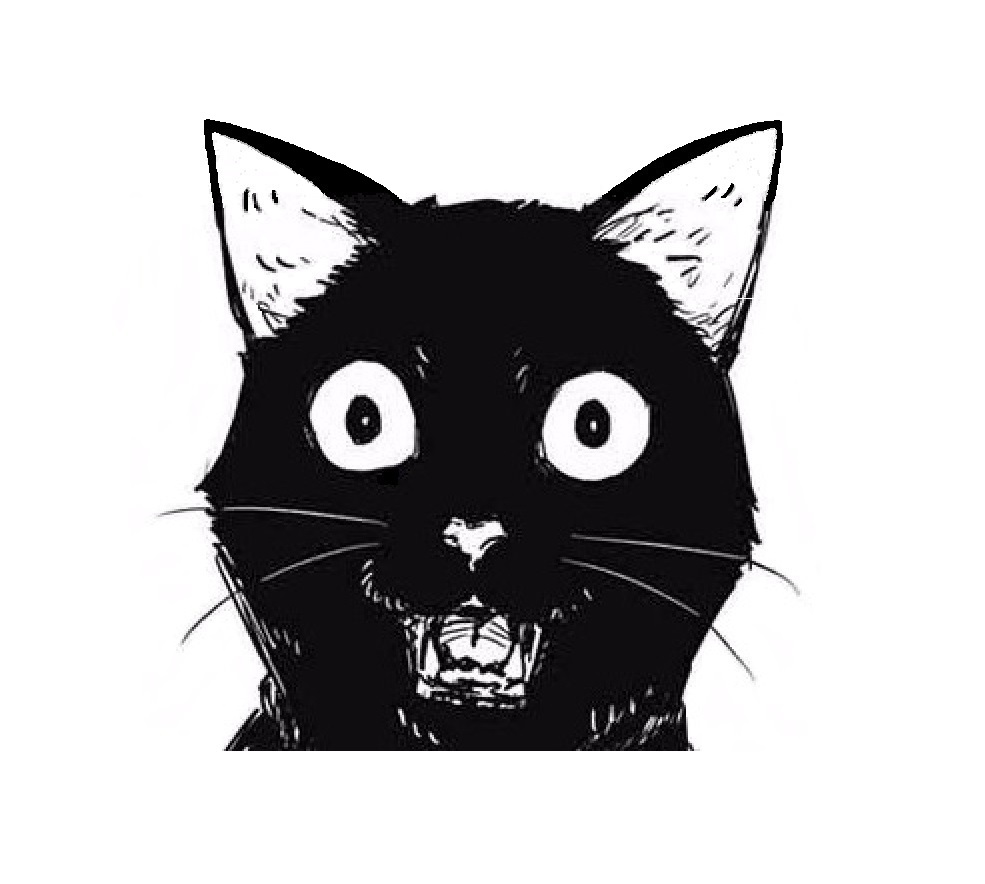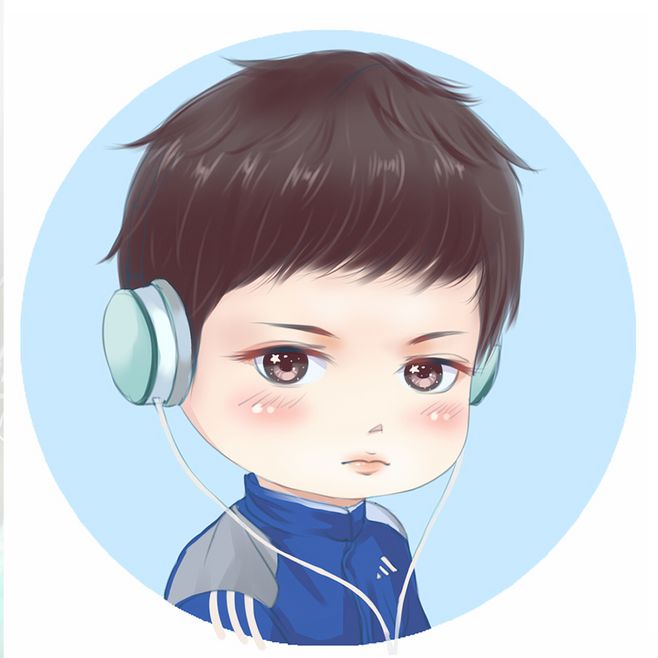一夜无眠。
窗外天刚蒙蒙亮,还远不到太阳升起的时辰,谭昭就用力掀开身上的被子坐起身,面色阴沉地看着紧闭的房门,等着林逍遥的人来叫他。
结果时间悠悠过了一个早晨,门外仍然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谭昭终于不耐烦了,拉开门就往外走。
不知是不是因为林逍遥手裡还握着另外一半解药的缘故,他一点也不担心谭昭跑了,谭昭在这间房裡待了一夜,他既没有找人看着他也没有从外面把门锁上。
谭昭漫无目的地在万霞谷中,错综复杂的廊道裡转,开始时走得怒气冲冲,恨不得见到林逍遥时把他按在地上打,结果一炷香后,愤怒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茫然。
在他第六次看到院裡那棵因是冬季,所以树杈上都是光秃秃的歪脖子树时,茫然变得深切。
他迷路了。
谭昭立在原地片刻,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,万霞谷可是宿影教的地盘,不是什麽谁家后院。虽然宿影教没了,但不代表建立在此处防御敌袭的阵法也没了。
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阵法天禅宗到处都是,从山脚一路埋到山顶上。
如果在此处的是虞明镜或是虞煊,破阵根本不在话下,但谭昭不行,他不会。
正当他苦思如何走出去时,耳边捕捉到了一点很小的声音。
声音确实很小,谭昭甚至来不及听清到底是什麽东西发出的就没了,好在他听出了大致的方位。
谭昭连一丝犹豫都没有,抬腿就朝声音来源走去。
他也不知自己去往的是何处,只是越往某处走,方才响起的声音便断断续续地传来,由细小变得清晰。
是瓷器碎裂的声音。
当谭昭穿过一扇月亮门进入一间院子后,大开的房门裡忽然被丢出来一隻白瓷小碗,就从他眼前飞快地掠过后砸在地上碎开一地的碎片,裡面的人正在发出歇斯底裡的吼叫,又或是发出像在哭又像在笑的声音。
虽未见其人,就这动静也能想象那人的癫狂。
一直等到裡面拆房子般的动静变小了谭昭才慢慢挪着小步子,背靠着院墙一点点蹭到门边,而后才小心翼翼地探出一隻眼睛从门框边上往裡看。
屋裡一片狼藉,所有的桌椅板凳全数被人掀翻在地,地上躺了很多或大或小的瓷片,有些沾了鲜红的血迹,看着分外触目惊心。
一个穿着单薄衣衫的人就这麽趴在满室狼藉中,散开的黑色长发披在身上,原本就过分瘦削的身体显得更加弱不禁风。
谭昭躲在门边看着那人趴在地上发出呜呜哭声,走不合适进去也不合适的,踌躇了一会儿后还是迟疑地对着裡面的人问:“……你没事吧?”
趴在地上的人听见他的声音浑身剧烈一颤,身体像深秋树上即将飘零的枯叶般开始簌簌发抖。
一看这人的反应谭昭就后悔了,头疼地挠挠自己的眉心,想了想也只能道:“你的脚流血了,得包扎一下才行啊。”
地上的人仍是趴伏着不动,因姿势露出的脚心血肉模糊,应当是方才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碎片。
谭昭见他一动不动,又忍不住看了眼他的脚心,忽地眉心一蹙,仔细地瞧了瞧那人脚后跟往上数寸之地一道看着不算旧的疤痕。
以愈合程度来看,应当是一年有余的时间。
谭昭默不作声地看完了他两隻脚上的疤痕,视线缓缓往上移,掠过他小腿上隐约露出裤腿的陈旧伤痕,想看看他的手腕。
视线刚从肩膀划过,落在头部的位置,谭昭就精确地对上了藏在乱发中的一隻眼睛。
在谭昭的注意力落在他脚上的伤口时,这人早已把埋在手臂上的脸缓慢地转过来一些,默默地盯着门外的谭昭。
一人藏在门外,一人趴伏在地上。
一隻眼睛对一隻眼睛。
静默了好一会儿,谭昭才听见这人用沙哑得像喉间裹了碎片残渣的声音问他。
“……你是谁?”
谭昭慢慢地眨了下眼睛,从门边走了出来,站在房门外,“我是谭昭。”
地上的人在看清了谭昭的脸,听见了他说自己是谭昭时,就不可置信地直起了身子,垂在身侧的双手还在微微颤抖。
谭昭终于得见此人的相貌。
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病态,苍白得没有丝毫血色的脸,眼下一片乌青,而且他太瘦了,瘦得几乎快脱了相,把一双本就不小的眼睛显得像要突出眼眶一般,细看还有点慑人。
可即使如此还是能隐约看出这人五官裡原先的清朗俊逸,想来若是能长点肉,好好修养一番,也应当是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。
“……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他这话说得可算十分奇怪,谭昭听得一愣,“啊?”
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见人不问出个答案就不消停的样子,谭昭隻好道:“有个人给我师傅下了毒,要我帮他办事,成了之后给我解药。”
他好像听不见谭昭说话,眼睛无神地望着谭昭,像在透过他看什麽人,嘴裡低喃,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谭昭知道自己现在说什麽他都听不进去了,又不可能对着这样一个人坐视不理,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抬脚走了进去,走到那人面前半蹲下身,“我扶你起来。”
那人还在问他,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Top
窗外天刚蒙蒙亮,还远不到太阳升起的时辰,谭昭就用力掀开身上的被子坐起身,面色阴沉地看着紧闭的房门,等着林逍遥的人来叫他。
结果时间悠悠过了一个早晨,门外仍然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谭昭终于不耐烦了,拉开门就往外走。
不知是不是因为林逍遥手裡还握着另外一半解药的缘故,他一点也不担心谭昭跑了,谭昭在这间房裡待了一夜,他既没有找人看着他也没有从外面把门锁上。
谭昭漫无目的地在万霞谷中,错综复杂的廊道裡转,开始时走得怒气冲冲,恨不得见到林逍遥时把他按在地上打,结果一炷香后,愤怒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茫然。
在他第六次看到院裡那棵因是冬季,所以树杈上都是光秃秃的歪脖子树时,茫然变得深切。
他迷路了。
谭昭立在原地片刻,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,万霞谷可是宿影教的地盘,不是什麽谁家后院。虽然宿影教没了,但不代表建立在此处防御敌袭的阵法也没了。
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阵法天禅宗到处都是,从山脚一路埋到山顶上。
如果在此处的是虞明镜或是虞煊,破阵根本不在话下,但谭昭不行,他不会。
正当他苦思如何走出去时,耳边捕捉到了一点很小的声音。
声音确实很小,谭昭甚至来不及听清到底是什麽东西发出的就没了,好在他听出了大致的方位。
谭昭连一丝犹豫都没有,抬腿就朝声音来源走去。
他也不知自己去往的是何处,只是越往某处走,方才响起的声音便断断续续地传来,由细小变得清晰。
是瓷器碎裂的声音。
当谭昭穿过一扇月亮门进入一间院子后,大开的房门裡忽然被丢出来一隻白瓷小碗,就从他眼前飞快地掠过后砸在地上碎开一地的碎片,裡面的人正在发出歇斯底裡的吼叫,又或是发出像在哭又像在笑的声音。
虽未见其人,就这动静也能想象那人的癫狂。
一直等到裡面拆房子般的动静变小了谭昭才慢慢挪着小步子,背靠着院墙一点点蹭到门边,而后才小心翼翼地探出一隻眼睛从门框边上往裡看。
屋裡一片狼藉,所有的桌椅板凳全数被人掀翻在地,地上躺了很多或大或小的瓷片,有些沾了鲜红的血迹,看着分外触目惊心。
一个穿着单薄衣衫的人就这麽趴在满室狼藉中,散开的黑色长发披在身上,原本就过分瘦削的身体显得更加弱不禁风。
谭昭躲在门边看着那人趴在地上发出呜呜哭声,走不合适进去也不合适的,踌躇了一会儿后还是迟疑地对着裡面的人问:“……你没事吧?”
趴在地上的人听见他的声音浑身剧烈一颤,身体像深秋树上即将飘零的枯叶般开始簌簌发抖。
一看这人的反应谭昭就后悔了,头疼地挠挠自己的眉心,想了想也只能道:“你的脚流血了,得包扎一下才行啊。”
地上的人仍是趴伏着不动,因姿势露出的脚心血肉模糊,应当是方才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碎片。
谭昭见他一动不动,又忍不住看了眼他的脚心,忽地眉心一蹙,仔细地瞧了瞧那人脚后跟往上数寸之地一道看着不算旧的疤痕。
以愈合程度来看,应当是一年有余的时间。
谭昭默不作声地看完了他两隻脚上的疤痕,视线缓缓往上移,掠过他小腿上隐约露出裤腿的陈旧伤痕,想看看他的手腕。
视线刚从肩膀划过,落在头部的位置,谭昭就精确地对上了藏在乱发中的一隻眼睛。
在谭昭的注意力落在他脚上的伤口时,这人早已把埋在手臂上的脸缓慢地转过来一些,默默地盯着门外的谭昭。
一人藏在门外,一人趴伏在地上。
一隻眼睛对一隻眼睛。
静默了好一会儿,谭昭才听见这人用沙哑得像喉间裹了碎片残渣的声音问他。
“……你是谁?”
谭昭慢慢地眨了下眼睛,从门边走了出来,站在房门外,“我是谭昭。”
地上的人在看清了谭昭的脸,听见了他说自己是谭昭时,就不可置信地直起了身子,垂在身侧的双手还在微微颤抖。
谭昭终于得见此人的相貌。
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病态,苍白得没有丝毫血色的脸,眼下一片乌青,而且他太瘦了,瘦得几乎快脱了相,把一双本就不小的眼睛显得像要突出眼眶一般,细看还有点慑人。
可即使如此还是能隐约看出这人五官裡原先的清朗俊逸,想来若是能长点肉,好好修养一番,也应当是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。
“……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他这话说得可算十分奇怪,谭昭听得一愣,“啊?”
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见人不问出个答案就不消停的样子,谭昭隻好道:“有个人给我师傅下了毒,要我帮他办事,成了之后给我解药。”
他好像听不见谭昭说话,眼睛无神地望着谭昭,像在透过他看什麽人,嘴裡低喃,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谭昭知道自己现在说什麽他都听不进去了,又不可能对着这样一个人坐视不理,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抬脚走了进去,走到那人面前半蹲下身,“我扶你起来。”
那人还在问他,“你怎麽会在这裡?”
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