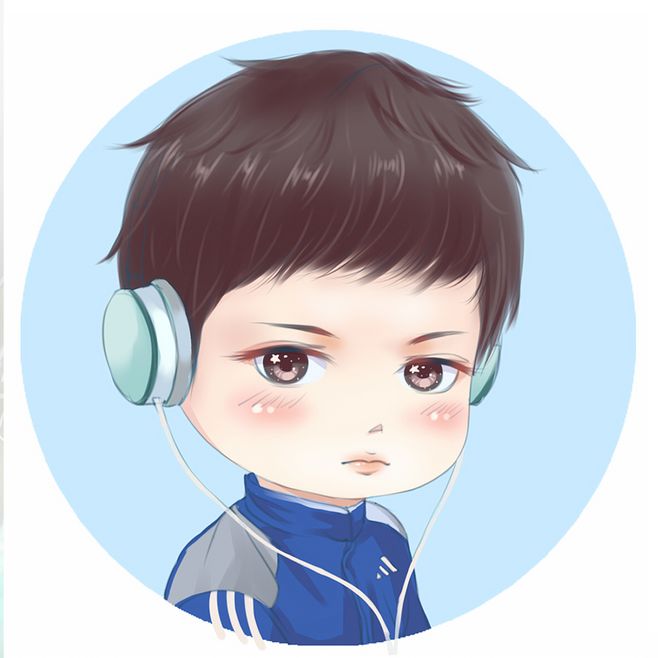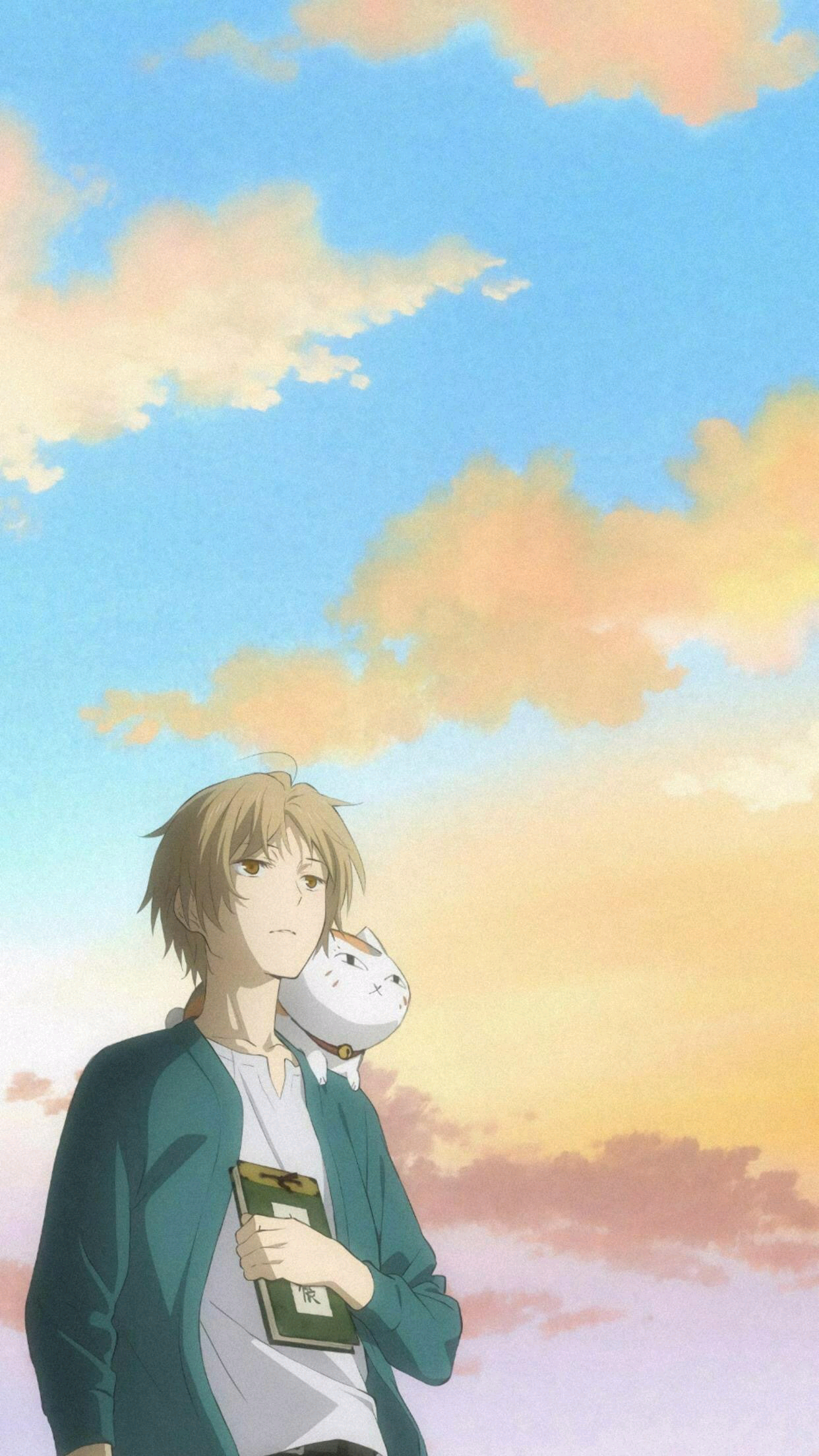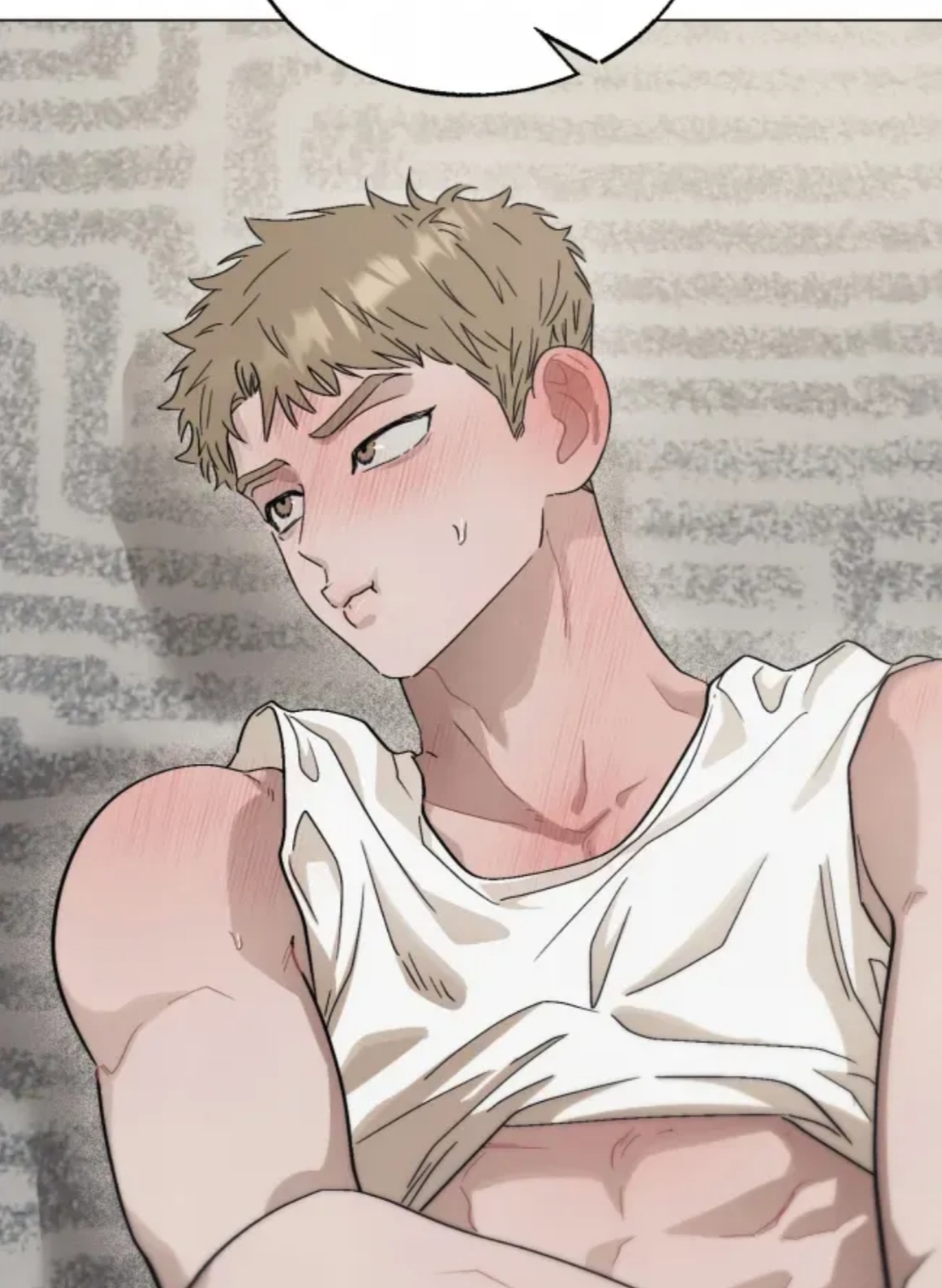自己差点满身“开花儿”这件事毫无自觉,此时正在嘴碎似的叨叨,“这不过片刻的功夫,你跑哪儿去了?多大的人了还撒手就没,你说说你,让不让人省心了?我看下回就该把你系我裤腰带上。” 舸笛:“…………” 舸笛:“你的伤?” 比起姜逸北这一堆没头没脑的嫌弃,舸笛比较惊讶的是姜逸北已经能够在屋顶起落了吗?他的伤好得这么快? 刚刚在城门口,下马车的时候是不是还非要等他扶来着? 姜逸北一时语塞。 要不是现在是真着急着赶去甲子客栈报信,估计他能现在立刻故意从墙头栽下去,以证清白。 至于怎么个“清白”,其实他伤确实还未曾好。只不过事出有因,这不是赶时间么,便能撑就撑着些了。反正他向来都挺能忍疼的。 但是这番话要是解释到舸笛面前,怎么看怎么像狡辩不是。 姜逸北这人比较异于常人。平日里胡说八道的时候嘴里一套一套的,但是这种看起来会像假话的真话,却又不愿意开口说了。 舸笛没等来回答,正待再问,结果姜逸北掐了一把舸笛的腰,“不许转移话题,说你走丢的事儿呢。” 舸笛不认帐:“……谁说我走丢了?” 姜逸北再掐了一把,“过会儿再找你算账。” 舸笛:“……撒开!横竖不是你疼是吧,没轻没重的。” 姜逸北笑,“撒开你就掉下去了,抓紧点吧你。” 姜逸北带着舸笛一路回了甲子客栈,进了客栈之后姜逸北将舸笛留在大堂,自己先行上去找了三叔。 舸笛便在大堂随便挑了个位置坐了下来,小二来上过茶,问过要不要吃些什么,便退下了。 坐下不过片刻,就有人在舸笛旁边停下了。 舸笛听着这走过来的脚步声觉得有些耳熟,却也一时想不起来具体是谁。此时有些迷茫的抬头,就听那人恭敬道,“少阁主。” 舸笛这才想起来这人。是之前姜逸北让人帮他送药藤的那个。舸笛要是没记错的话,叫做邱欢。 之前展安也曾说过,此人因为不在暗花榜内。所以软禁在甲子客栈不得出门,所以在此碰到也算正常。 舸笛略一点头,道,“药藤的事辛苦你了。” 邱欢本就不是个话多的,只简略道,“少阁主言重。” “此处不用唤少阁主,”舸笛说罢,又道,“坐吧。” 邱欢略一犹豫,还是在舸笛的桌边坐了下来。 舸笛帮人倒了一杯茶,推过去,“这段时间你一直在不染城,云叔可曾联络过你?” “不曾。”邱欢答完沉默了一下,又道,“云叔为何要联络我?” 舸笛道,“说来话长。” 倒也不是说来话长,不如说是这地方人多口杂,不适合谈及此事。 邱欢倒也知道轻重,瞬间反应过来了,不再追问。而是转头向舸笛汇报了一些近来所见,主要是唐三叔与不染城的近况。 正说着,那边从楼梯上下来一个人,斜挎着一个药箱,气质温和,不过脸色却有些病态的苍白。此人正是柳倚春。 他刚刚过来给三叔复诊,恰巧遇见姜逸北进去。他看姜逸北的脸色,估计是有什么事情要密谈,自己便避嫌提前出来了。 他在楼梯上就看见了正在喝茶的舸笛,一时还有些惊讶,不知这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了。 于是挎着药箱便走了过去。 舸笛对柳倚春的脚步声熟悉些,所以人还未到,舸笛便朝着柳倚春的方向点了个头。这边邱欢也跟着看过去,正在汇报近况的声音也自觉停下了。 柳倚春坐下便道,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不是回玄机阁了吗?” 舸笛笑了一下,“有事回来一趟。” 柳倚春一点头,只当舸笛复仇之事还未来得及开始,此时便道,“回来就好,不染城终归还是安全些。而且旧事已过,楚蹊应当也是希望你好好活着的,不必非要复仇。” 舸笛冲着柳倚春笑了下,心知反驳无用,所以并没有开口反驳。倒是柳倚春瞧着舸笛的面色似乎有异,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他与舸笛在这不染城中待了三年,舸笛身上的伤病都是他一手负责的,所以柳倚春对舸笛的异状总是格外敏[gǎn]一些。 柳倚春看了两眼,突然道了一声“得罪”,然后伸手搭在了舸笛的手腕,二话不说就开始切脉。 舸笛一怔,倒是也没挣脱。 他也没想到柳倚春居然会第一眼就看出他身上有问题。毕竟蓉蓉姑娘专门诊治了一番,也没查出什么来。 只是中毒的事实在不适合在大堂声张,他便让旁边坐着的邱欢去找掌柜的要了一个房间。横竖今晚也是要在这里住下的,也用得上。 柳倚春瞧着邱欢听话地去柜台的模样,“原来他是你的人么?我听说是他将药藤送进不染城的。” 舸笛也没否认,“是姜逸北取的药藤,交由他送进来的。” 柳倚春点头,没太大的兴趣,也没细想姜逸北把药藤给了邱欢自己做什么去了。 只专心手下的脉象,并道,“最近可有什么不适?” 舸笛犹豫了一下,还是老实道,“不久前曾有脏腑绞痛于夜间发作。” 柳倚春又道,“可是内伤?” “不是,”舸笛顿了一下,道,“此处说话不便,待会儿说罢。” 柳倚春收回了手,道,“听你这语气,似乎是知道你身体怎么回事?” 简直不能再清楚了。舸笛心道,怕是接下来不是请你看病,而是请你帮忙排算死期。 转眼邱欢就就已经办妥了。有小二来带舸笛与柳倚春上楼。 进了房,关了门,舸笛才把自己中毒的事情掐头去尾说了一下。 倒也没多具体,他料想柳倚春应当也不关心那些细节,只粗略说了自己误入先辈安寝之地,中了毒,以先辈留下的讯息来看,怕是活不了多少时日。 柳倚春听罢,又再诊查了一遍,却没有给具体的结论,只不过神色确实不大好看。 想来这毒也确实不是什么善茬儿。 舸笛倒是想得开,压根不问“这毒能不能解,怎么解”,直接开口问“大约还有多少时日”。 柳倚春道,“你时日还久。要真想知道这事儿该去问算命的,不该来问我。” 听柳倚春这语气就知他现在的心情是不大好的,舸笛也就跟着笑了笑。然后道,“你还记得蓉蓉吗?” 柳倚春:“蓉蓉?” 舸笛:“她托我带话,说是你留下的药摊子她帮你看着了,若是空闲便回去看看吧。” 柳倚春听及旧人,坏心情散了些,换成了一个苦笑。 这哪里是空闲不空闲的事,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弱大夫,出不染城怕就难有命在了。 所以此时也只能感叹一句“倒是让她受苦了”。 两人正说这话,门突然“吱呀”一声被推了开,连个敲门声的预警都没有。 姜逸北从门外走进来,半点没有自己乱闯的自觉,口上揶揄道,“我还以为你在方寸大小的大堂里迷路了,我这才上去多久你就没人影了。” 他已经去确认过三叔的身体状况,毒已经解了,只是还有余毒未清。而且这毒凶猛,影响不小,身体损耗颇大。但是能保住手脚性命也算是好的了。 毕竟元气亏损还可以慢慢养,手脚要真烂成水了那可是怎么都补不回来了。 他与三叔说过孔遥之事。却没想到三叔居然先他得到讯息。 因为孔遥是以自己的身份进的不染城,所以很快城内就得了讯息,沈右以木鸟将这讯息传给了三叔。 之前展安被沈右召过去,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 既然城内已经有了防备,姜逸北就安心许多。只简略和三叔说了几句紧要的,便重新回到大堂去寻那瞎子了。 结果在大堂左右转了半天也没瞧见人,问了楼下掌柜的才知道这人上楼来了。 姜逸北也不需要人邀请,直接就在舸笛旁边坐下,与柳倚春打过招呼,便问起了舸笛的情况。 柳倚春正待开口,就听得舸笛咳嗽了一声。柳倚春刚刚口张到一半,愣住了。 姜逸北看着这人当着自己的面,明目张胆地给人递暗示。忍不住动脚,在桌子底下不轻不重地踢了一下舸笛的小腿肚,不满道,“你咳嗽什么?”╩思╩兔╩网╩ 舸笛把腿往旁边让让,脸不红心不跳地道,“嗓子不舒服。” 姜逸北:“…………” 姜逸北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茶壶,是刚刚小二上来引路的时候换过的。于是翻开一个茶杯,给人倒了杯茶,“那就多喝水。” 姜逸北转过头来,“柳先生你接着说。” 柳先生:………… 柳先生觉得自己很多余。 刚刚踢的那一脚,不轻不重的,也不见狎暱。但是比起一般的朋友动作,却又多了几分不可说的味道。 柳倚春莫名也跟着咳嗽了一声,主要是为了缓解尴尬。 因为刚刚舸笛的暗示他已经接收到了,便只含蓄道,“暂且看不出什么大碍。” 不是“没有大碍”,是“看不出”。 只是姜逸北也一时没注意细分用词,此时也只是疑惑着道, “怎么会?那日早上我看他脸色差得好似新坟里爬出来的。” 柳倚春听罢,不禁正色了几分,忙问道,“可还有别的症状?” 大夫讲究“望闻问切”,只是舸笛毒发的时候柳倚春不在,舸笛自己也瞧不见自己怎么个样子,只能从别处寻了。 姜逸北细细回忆了一下,皆说与柳倚春听了。 柳倚春还是没当场下结论,只是陷入沉思。 姜逸北比舸笛自己都要紧张,跟等待宣判似的等着柳倚春说出个一二三四来。 结果柳倚春却站起身,道,“回春馆还有些事,我先回去了。”然后便站起身匆匆走了。 姜逸北瞧着柳倚春的背影,道,“一看就是回去查医书了,果然兔子的朋友也是兔子。” 都是不会骗人的。 舸笛没接话,安安静静地喝着姜逸北给自己倒的茶。 姜逸北转过头来,看着自己旁边这个乖乖巧巧的,“要不你老实点,主动给我说说。”第64章 啊,想欺负他 舸笛正在思索着怎么把这个事情给绕过去的时候,突然城中响起了钟声。 舸笛和姜逸北两人皆是一愣。 钟声既响, 就必是有外敌来袭。 姜逸北第一个反应便是孔遥, 但是随即就否决了。 孔遥既然说进城为他和唐三叔, 那便应该是真的, 姜逸北没觉得他是在说谎。 他若去找三叔, 两人同是暗花榜上的人, 正当进入不染城, 所以生死天定。这是个人恩怨,不需要鸣钟示警。 鸣钟之事,皆是共同

首次打赏者皆可获得专属头像框~